- 相關推薦
張舜徽先生歷史文獻學成就述要
對歷史文獻加以整理和研究,是中國最古老的一門學問。而歷史文獻學作為一個學科 納入歷史科學的體系之中,則不過數十年時間。已故著名歷史學家張舜徽先生對這個學 科的確立,起到過重要作用。回顧他對歷史文獻學理論的若干認識及其實踐,對我們今 天探討新世紀歷史文獻學的學科建設及發展方向,不無啟迪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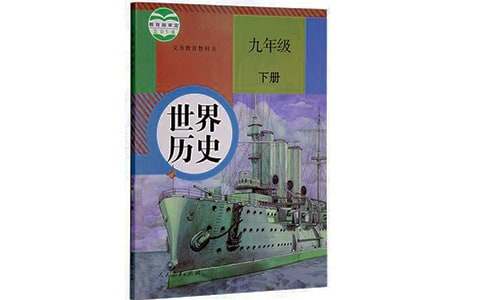
究校讎學古義 闡述學術淵源流別
張先生的第一部學術著作,是30歲剛出頭時寫就的《廣校讎略》。顧名思義,書中內 容是推廣發揚宋代鄭樵的《通志·校讎略》,自然是一部文獻學著作。其自序稱:“少 時讀書,酷嗜乾嘉諸儒之學,寢饋其中者有年。其后涉獵子史,兼覽宋人經說,見書漸 廣,始@①然不自慊,泛濫群籍,于漢、宋諸儒,獨宗二鄭,以為康成經術,漁仲史裁 ,譬諸靈海喬岳,無以益其崇深。兩家涂轍雖殊,而所以辨章學術之旨則無不同。”于 是,“溫經校史,流覽百家,窮日夜不輟,積之十年,始于群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 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稍能辨其原流,明其體統”。[1](P1)從這段話,可以窺見 張先生的學術趣向。書中形成的若干見解,為其一生所恪守。所以,這部書雖僅10萬余 言,卻是他一生學術探索的一個堅實的基點。
《廣校讎略》凡5卷,分為19論100篇。其中尤可注意者,為以下3論30篇:
其一,“校讎學名義及封域論二篇”。近世學者于審定書籍之際,約分三途,即目錄 學、版本學、校勘學。張先生上承鄭樵、章學誠、朱一新的見解,主三者之合,其首篇 《目錄板本校勘皆校讎之事》論述說:“校讎之事,始于周宣王時宋大夫正考父校商名 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秦火之后,書尤殘缺,漢成帝時詔劉向等校書秘閣 ,此業乃稱專門。校讎之名,亦自劉向定之,所謂‘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 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讎’是也。向每校一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 其訛謬,隨竟奏上。后又集眾錄,謂之《別錄》,蓋即后世目錄解題之始。向校書時, 廣儲副本,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有所謂臣向書, 有所謂臣某書,博求諸本,用以讎正一書,蓋即后世致詳板本之意。觀向所為《戰國策 敘錄》云:‘本字多脫誤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然則向校讎時,留心文字訛 誤之是正,蓋即后世校勘之權輿。由此論之,目錄、板本、校勘,皆校讎家事也。但舉 校讎,自足該之。語其大用,固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次篇《目錄學名義之非》論 述清代以目錄自雄之士,“校其所至,上者但能校勘文字異同,審辨板片早晚耳,蓋已 鄰于書賈之所為,難與語乎辨章學術之大。”在引述章學誠、全祖望的有關論述后,張 先生發出如下議論:“夷考世俗受病之由,蓋原于名之不正耳。夫目錄既由校讎而來, 則稱舉大名,自足統其小號。自向、歆父子而后,惟鄭樵、章學誠深通斯旨,故鄭氏為 書以明群籍類例,章氏為書以辨學術流別,但以校讎標目,而不敢取目錄立名,最為能 見其大。”
張先生關于目錄版本校勘不必獨自稱“學”的觀點,學者中有不同的看法。不過,這 一點并不重要。他稱舉校讎的大名,旨在強調三者的聯系,達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的目標。這一學術宗旨,是大家都認同的。他關于文獻學的若干理論建樹,便是他上 推校讎古義、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思辨成果。
其二,“著述體例論十篇”。跟一般的著述體例介紹不同,張先生論著述體例,旨在 對諸類典籍作推本潮源的探討。只看10篇標題,便一目了然。如“古人志在用世不得已 而后著述”、“古代著述皆可目為史料”、“擬古著書之始”、“著作編述鈔纂三者之 別”、“編述體例”、“太史公書為編述之正體”、“鈔纂之書日盛而后著述日衰”、 “官修之書無關著述”、“施教之書與著述異體”,涉及到大量古書的起源及其流別, 他在博覽群書后,自出機杼,加以論斷。這里,僅舉《著作編述鈔纂三者之別》一篇為 例。張先生發揮王充《論衡·對作篇》中的群書區分法,認為“載籍極博,無逾三門: 蓋有著作,有編述,有鈔纂,三者體制不同,而為用亦異。名世間出,智察幽隱,記彼 先知,以誘后覺,此之謂著作;前有所因,自為義例,熔鑄眾說,歸一家言,此之謂編 述;若夫鈔纂之役,則惟比敘舊事,綜錄異聞,或訂其訛,或匡其失,校之二科,又其 次也。”以先秦兩漢著述而論,《五經》前無古人,可謂著作;《史記》《漢書》前有 所因,而在熔鑄剪裁后成為一家之言,可謂編述;桓譚《新論》、王充《論衡》則在比 敘舊事、綜錄異聞之類,屬鈔纂之書。
對群書作了這樣的區分,張先生認為可以使讀者知道學術之深淺,意義不小。“試循 時代以求之,則漢以上之書,著作為多。由漢至隋,則編述勝。唐以下雕板術興,朝成 一書,莫登諸板,于是類書說部,充棟汗牛,盡天下皆鈔纂之編。昔人每教學者多讀唐 以前書,非貴遠賤近,蹈人情之通患而不知返也,誠以先唐之書,多關作述,猶少空言 。唐以下雜鈔日廣,語皆枝葉。本末先后高下淺深之分,學者所宜詳辨也。”[1](P8-9 )
其三,“漢唐宋清學術論十八篇”。張先生強調校讎學的功用在于“辨章學術,考鏡 源流”,因而他的目光便不僅僅停留在正史藝文志經籍志、官私目錄上,yín@②y ín@②于版本早晚,汲汲于考訂文字異同,而是集中精力,把握學術發展趨勢,明辨 各類著述的脈絡源流。“漢唐宋清學術論”在諸論中,篇幅最長。從辨章學術始于太史 公、鄭玄校注群經實寓辨章學術之意、經師家法亡于東漢、唐初諸儒論學有不同于后世 者、唐代史學實有承先啟后之功、昌黎韓氏實開兩宋學風、宋史分立儒林道學二傳之故 、兩宋諸儒實為清代樸學之先驅、宋人經說不可盡廢、宋世私門校書之盛,到清代興起 之師、乾嘉諸儒囿于治經之弊、乾嘉諸儒著述非初學所能讀、道咸以下清學漸衰、道咸 以下學者依附乾嘉之弊與模擬著書之非、群經新疏未必盡善、專精與博通之辨,各個專 題,皆一一扼要論述。可以說,這實際上是一部提綱挈領的文獻學史。從漢至清兩千年 中的文獻整理與研究狀況,都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角度,舉列在這里了。張先生 首正校讎之名,起到了綱舉目張的作用。
另外70篇,為著述標題論8篇,作者姓字標題論5篇,補題作者姓字論4篇,援引古書標 題論8篇,序書體例論5篇,注書流別論2篇,書籍傳布論2篇,書籍散亡論2篇,簿錄體 例論4篇,部類分合論7篇,書籍必須校勘論2篇,校書非易事論4篇,校書方法論6篇, 清代校勘家得失論3篇,審定偽書論3篇,搜輯佚書論5篇。單從篇目,已足見內容之豐 富。
對《廣校讎略》中的見解與內容,張先生后來又有所發揮與擴展。為了指導后輩校讀 古籍,他在50歲時寫出《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一書。全書分為通論、分論、附論三部 分。由于分論的篇幅較多,又分為上下,共成四編。第一編,通論校讀古書的基本條件 ,從識字談起,以至辨識版本諸問題。第二編分論上,專談校書,涉及到校勘的必要性 、校書的依據和方法等文獻學理論問題。第三編分論下,專談讀書方面的問題,論述了 古人寫作中的一般現象和古人著述體要,提出了閱讀全史的重要性和具體讀法,歸納了 整理史料的一般方法。第四編,附論有關辨偽和輯佚方面的問題。全書寫作的初衷雖只 是普及文獻學知識,但持論謹嚴,內容豐富,在文獻學理論的研究上有所發展。如論輯 佚書,首先從書籍本身的產生、發展、變化,從社會的變遷分析古書散佚的原因,然后 闡述輯佚作品的展開和取材的依據,并歸納出五條途徑和方法,即取之唐宋類書,以輯 群書;取之子史及漢人箋注,以輯周秦古書;取之唐人義疏,以輯漢魏經師遺說;取之 諸史及總集(如《文苑英華》之類),以輯歷代遺文;取之一切經音義(以慧琳《音義》 為大宗),以輯小學訓詁書。張先生還從過去學者在輯佚工作中所犯的錯誤(漏、濫、誤 、陋等),指出讀者在閱讀中應注意的問題,并告誡初學者:“至于自己動手搜輯佚書 ,更是學問成熟以后的事。因為讀書不多,見聞不廣,雖對這方面有興趣,但難免掛一 漏萬。加以這種工作,做起來很費時間,耽誤了讀書的歲月,尤為可惜。初學似不必在 這里面投下太多的勞動,等到業務基礎打好以后,再談此事,比較容易著手。”[2](P3 10)
書中此類見解甚多,以致顧頡剛先生稱贊此書“綱舉目張,顯微索隱,為初學引導正 路,諄諄以教,苦口婆心,俾其于摸索之中,得見明燈。”[3](P405)
賦文獻學新意 建構學科理論體系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學術界歡呼進入“科學的春天”的時期,張舜徽先生恰 好在此時進入到他學術研究的豐收季節。1979年,他與學界同行在桂林發起,成立“中 國歷史文獻研究會”,被推舉為會長。1980年,國務院頒布學位條例,他隨之被評為全 國首位歷史文獻學專業博士導師。客觀形勢催促著他繼續思索,為歷史文獻學的學科建 設提出系統的理論與方法。不久,他就完成了學科建設的奠基之作——《中國文獻學》 。這部書的主要貢獻,在以下幾方面:
一、確定文獻學的范圍和任務
在20世紀,最早以“文獻學”名其書者,為鄭鶴聲、鄭鶴春先生的《中國文獻學概要 》。他們認為:“結集、翻譯、編纂諸端謂之文;審訂、講習、印刻諸端謂之獻。敘而 述之,故曰文獻學。”[4](P1)從全書內容看,涉及的是文獻整理的一些問題,和真正 意義上的文獻學還有一段距離。60年代,王欣夫先生的《文獻學講義》,主要是目錄、 版本、校勘的知識介紹。張先生在《中國文獻學》中,開宗明義,就是確定文獻學的范 圍和任務。他從“文獻”原來的含義和范圍出發,認為文獻應該是流傳下來的文字資料 。“至于地下發現了遠古人類的頭蓋骨和牙齒,那是古生物學的研究范圍;在某一墓葬 中出土了大批沒有文字的陶器、銅器、漆器等實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時代和手工藝 的發展情況,那是古器物學的研究范圍。這些都是考古學家的職志,和文獻學自然是有 區別的。”進而,他指出:“我國古代,無所謂文獻學,而有從事于研究、整理歷史文 獻的學者,在過去稱之為校讎學家。所以校讎學無異成了文獻學的別名。凡是有關整理 、編纂、注釋古典文獻的工作,都是由校讎學家擔負了起來。”“我們今天,自然要很 好地繼承過去校讎學家們的方法和經驗,對那些保存下來了的和已經發現了的圖書、資 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簡、帛書),進行整理、編纂、注釋工作。使雜亂的資料條理化 、系統化;古奧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進一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條別源流, 甄論得失,替研究工作者們提供方便,節省時間,在研究、整理歷史文獻方面,作出有 益的貢獻,這是文獻學的基本要求和任務。”
在提出基本要求和任務后,張先生認為這還不夠,應該在整理、研究的基礎上寫出總 結性的著作來。“只要我們不是為研究而研究,為整理而整理,而是心懷大志,朝著一 個宏偉目標而努力不懈,不僅大有出息,而且可以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5](P3-4 )
二、總結前人整理文獻的經驗和業績
書中,用四編介紹古代文獻的基本情況,以及整理古代文獻的基礎知識——版本、校 勘、目錄。雖然他人書中也有同樣的內容,但張先生寫得簡明扼要,很有特色。他還概 括前人整理文獻的具體工作,像抄寫、注解、翻譯、考證、辨偽、輯佚等;歸納前人整 理文獻的豐碩成果,像修通史、纂方志、繪地圖、制圖表、編字典、輯叢書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重點介紹歷代校讎學家整理文獻的業績,通過他們的事跡來體 現文獻學的豐富內容。從漢至清,他介紹了劉向劉歆父子、鄭玄、陸德明、鄭樵、章學 誠、紀昀等人的成就。比如鄭玄,張先生認為歷來把鄭玄看成是一位經學家,是漢代經 學的集大成者,這是不夠的;他認為鄭玄所整理、注釋的書,不限于六藝經傳,也還注 《緯》,注《律》,可算是在整理古代文獻方面,做了極其廣泛而又深入的工作。“經 學”二字,本不足以范圍他。又如唐代陸德明,他在校理群書的基礎上,對厘析異同, 審定高下,取得很大成績,其巨著《經典釋文》是涉覽幾百家音義專著、取長補短而寫 成,它不僅是考證舊音的淵藪,而且保存古文異體,使經傳起源、傳授本末、注家姓名 、音義述造,一一詳敘。“《經典釋文》的《序錄》部分,乃是全書的綱領,寓有‘辨 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微意。”[5](P250)
對于清代替他人考試證學家整理文獻的業績,張先生也從語言文字、經傳、史實、周秦諸子四 個方面,進行了總結,使讀者對于清人的業績,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對近代學者,他 肯定整理文獻最有貢獻的人,一為張元濟,一為羅振玉,皆列舉大量的事實,使人心悅 誠服。這些,都是以介紹前人業績的形式,示人以整理文獻從入之途。
三、提出今后整理文獻的重要工作
對于整理歷史文獻,張先生認為,不是單純地校勘,注釋幾本書就完了。“更重要的 ,在能從叢雜的資料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將內容相近的合攏來,不同的拆出去, 經過甄別審斷、整理纂集的過程,寫定為簡約可守的新編。讓人們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化 方面,能夠節省時間、精力,較有條理有系統地了解過去,這誠然是文獻學工作者的重 任。”[5](P343)比較迫切的任務,他認為有4項,即甄錄古代遺文、改造二十四史、整 理地方志書、融貫諸子百家。
所謂甄錄古代遺文,就是對流傳至今的典籍,要詳辨其真偽。真偽可以分開的,應重 新寫定,加以整理。如《尚書》,只應把確切的28篇匯編在一起。古書中還有一些專門 性的單篇文字,如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的說明書《禹貢》在《尚書》內,專談科技制造 的《考工記》在《周禮》內,記載時令氣候的《夏小正》在《大戴禮記》內,諸如此類 的文字,非常寶貴,“自可從原書中抽出來,加以整理和闡述。”[5](P345)
所謂改造二十四史,有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內容方面“首先宜將后人附加的話,以及 錯簡、衍文、注語竄入正文等不符合原文的現象,加以改正刪訂,重新寫定。”“其次 ,便是整理舊注的問題。”[5](P348-349)要對舊注有所損益,同時舊注還有個排列的 形式問題。此外,對于世稱“蕪雜”的《宋史》,要有改修氣魄。
所謂整理地方志書,意思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方志名目繁多,而其中的“州縣 志”,記載比較詳盡,內容比較豐富,可供采摭的資料很多。“整理方志,必須首先在 這方面多下功夫。”其次,一些正史中不詳的社會制度、禮俗習尚、民生利病資料,尤 其是少數民族的史實,應“擇取其中最為重要的材料,分類撮錄,然后纂輯成書,寫出 一部可供采摭的史料叢編。替撰述理想中的中國通史提供素材,作出貢獻。”[5](P355 -356)
所謂融貫諸子百家,是指對周秦諸子加以研究,“找出他們對某一問題的共同認識, 由此考明問題的實質以及對當時和后世所起的作用。”[5](P357)對于兩漢以后的子書 、文集、筆記,區別其高下淺深,“假如我們能就歷代文集中甄錄出許多有價值的政治 論文,都為一集,何嘗不可繼《明經世文編》、《清經世文編》之后,編出《宋經世文 編》、《唐經世文編》、《先唐經世文編》呢?”對明清文集,“假如我們能分類輯錄 ,也可編出一些專門性的《叢鈔》,如前人所輯《經義叢鈔》之類,這自然是極有意義 的工作。”[5](P359-360)此外,對諸種筆記,也要有所甄別,凡是“樸學功深,富有 價值的,自當進行綜合整理。”[5](P361)
除了專著,張先生晚年有若干篇文章,都對80年代初興盛起來的古籍整理工作提出了 通達的見解,其中有不少富有啟發性的建議。這也屬于他建構文獻學理論體系的具體工 作。他的最基本的主張,是強調整理古籍不單是標點注釋校勘,而應該包括研究成果、 總結性論著,整理古籍的方法與門徑應包括論著、編述、注釋、鈔纂四個方面。[3](P1 32-134)一句話,古籍整理與研究必須結合起來,以使整理工作達到更高的水平。
80年代初期,張先生還選編過一部《文獻學論著輯要》,旁搜博求古人近人文獻學專 論凡120目。其自序中指出:“整理文獻,必先于群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 子集之支分派別,辨其原流,明其體統,然后能識古書之真偽,審版本之先后;旁及校 勘、目錄、輯佚、避諱諸端,皆當洞達其理,庶幾有著力處。若于此類全無所知,遽談 古籍整理,將見其昏昏冥冥,不解何從下手也。”[6](P1)《輯要》之作,在一定程度 上解決了古籍整理工作者“何從下手”的困難。
傾數十年心血 撰作文獻研究名篇
張舜徽先生不僅長期探討文獻學理論,而且身體力行,實踐自己的文獻學觀點,在整 理研究歷史文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為學術界貢獻了若干文獻研究的佳作。大體說來, 偏重于對文獻本身加以整理研究者有以下幾個類別。
一、通釋類
在目錄類著作中,《漢書·藝文志》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張 先生對二書皆作了逐句箋釋工作。于前者為《通釋》,于后者為《提要敘講疏》。
《漢書藝文志通釋》是在早年《釋例》的基礎上寫成的。張先生自少愛讀《漢書·藝 文志》,常置案頭,時加箋記,欲疏證全書。至晚年重溫是書,復有箋記,于是加以整 理,成《通釋》一書。這是一部“循文通釋”的疏證之作,“凡前人之說有可取者,悉 甄采之,句讀之有誤者正之,史證之偶疏者補之,亦間附論說以評斷之。”[7](P1)如 《六藝略》一開頭,就對通常的標點“《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提出異議 ,認為“此應讀‘《易》’字自為句,乃冒起下文之辭。”做了一番論證后,又推尋“ 經”的本義,認為“經者綱領之謂,原非尊稱。大抵古代綱領性文字,皆可名之為經。 ”[7](P10)隨之又解說“經十二篇”的篇名與內容、漢代《易》學的傳授情況、“施、 孟、梁丘三家”的盛衰。這種立足于史實而有見識的疏證,與一般的文字疏通不可同日 而語,對讀者掌握學術的變遷大有裨益。
《四庫提要敘講疏》是在課堂講稿基礎上整理而成。其自序稱:“往余為大學文科講 授‘國學概論’,即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敘》四十八篇為教本。昔張之洞《yóu@ ③軒語》教學者曰:‘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余則以為 此四十八篇者,又門徑中之門徑也。茍能熟習而詳繹之,則于群經傳注之流別,諸史體 例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衍,釋道之演變原委,悉了然于心,于是博治載籍,自不迷于 趣向矣。因與及門講論而疏通證明之。首取《提要》本書以相申發,次采史傳及前人舊 說藉資說明,末乃附以愚慮所及而討論之……迨講畢,始自錄所言,述為《講疏》。” [8](P1643)《講疏》不是一般的文字注釋,而以發表見解為主。如《提要》首句:“經 稟圣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講疏》云:“此昔人尊 經崇孔子之說也。自司馬遷以來,儒者莫不言孔子刪《詩》、《書》,定《禮》、《樂 》。然無征于《論語》,復不見于孟、荀,秦火以前,無此說也。《論語》為孔門所記 ,于其師一言一行,乃至飲食衣服之微,喜樂哀戚之感,無所不記。使果有刪定之弘業 ,何其弟子無一語及之?史遷嘗稱‘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 ,然《管子》中已云‘澤其四經’,可知以《詩》、《書》、《禮》、《樂》為教者, 不自孔子始。此四經者,皆舊典也。孔子特取舊典為及門講習之,所謂‘述而不作’也 。善夫龔自珍之言曰:‘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率弟子 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必具此識,而后可以不為俗說所惑。蓋自漢世罷黜百家,獨 崇儒術,言及六籍,必推尊孔子所刪定,此猶言易卦者,必托名于伏羲;言本草者,必 托名于神農;言醫經者,必托名于黃帝;言禮制者,必托名于周公;莫不高遠其所從來 ,以自取重于世,后先相師,如出一轍,學者可明辨之。”[8](P1648-1649)這樣的疏 釋,明顯是在做學術源流的考辨工作。
二、敘錄類
敘錄類的代表作是《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的文集甚多,張先生30多年中所寓目者, 便有1100余家。不用說,數量如此之多的文集,不是一般人所能讀到,即使能夠讀到, 也不一定抓得住要領、理得出頭緒來。張先生有感于劉向校書時寫作敘錄的深意,每一 文集讀畢,便考訂作者行事,記錄書中要旨,推究其論證得失,核定其學識深淺,各為 敘錄一篇,欲附以校讎流別之義,以推見一代學術的興替。最后,他從寫出的670多篇 敘錄中,選出價值較高的600家,匯為《清人文集別錄》24卷。這600家文集以儒林、文 苑中人物為多,大抵清人在碑傳志狀、刻書序跋、金石跋文以及詁經、證史、議禮、明 制、考文、審音、詮釋名物等方面有價值的文集,都收羅進來了。而于諸家考證之語, 凡論斷審密,確有發前人所未發者,皆特為拈出,著意介紹。全書的編排,略依時世先 后,系聯而下,其有家學、師承或友朋講習之益者,務令比敘,以見授受濡漸之跡。可 以說,這是一部罕見的匯集清人文集精華的提要性質的佳作。以至出版后,受到學術界 的交口稱贊。著名學者顧頡剛先生在評價此書與《廣校讎略》時說:“先生所作諸書, 示學者以途徑。啟牖之功,實在張香濤《yóu@③軒語》、《書目答問》之上。然彼 二書,對我輩之效用已極巨。先生別白是非,指明優劣。上紹向、歆之業,下則藐視紀 昀之書,其發生影響之大,固不待言也。”[3](P406)張先生另有一部《清人筆記條辨 》,可算是敘錄的變體。清人的筆記,雖不及文集之多,張先生幾十年中所寓目者,也 有300多家。若無別擇去取,則榛蕪不翦、靡所取材。于是,張先生對那些專載朝章禮 制、但記掌故舊聞、講求身心修養、闡揚男女德行、談說狐怪、稱述因果等等之類的筆 記皆屏不取,而對一些學涉專門、宜有專書以集其成的亦所不取。經過這樣的篩選,最 后收書100家,分為10卷,略依時世先后而編排。每家皆先述其生平,而后言其著述。 因筆記體裁與文集有別,張先生所做工作,也與《別錄》有些差異,即“擇其義之可采 者,分條件系,加以考辨,亦有綜述而論列之者。”[9](P1)書中所錄百家筆記之言, 有辨章學術者,有考論經術者,有證說名物制度者,有訂正文字音義者,有品定文藝高 下者,有闡述養生方術者,得失互見,多可商榷。為平亭是非,張先生“凡遇精義美言 ,則為之引伸發明;或值謬說曲解,則為之考定駁正。”[9](P2)對清人筆記的這種條 辨形式,可以說是“敘錄”的一種創造性運用。
三、校注訓詁類
對于基本典籍,張先生用功尤深。閱讀過程中,做了不少校注和訓詁工作。比較系統 的成果,收載在《舊學輯存》中的,計有11種,即《唐寫本玉篇殘卷校說文記》、《爾 雅釋親答問》、《小爾雅補釋》、《急就篇疏記》、《異語疏證》、《釋疾》、《字義 反訓集證》、《兩戴禮記札疏》、《讀書箋釋之余》、《敦煌古寫本說苑殘卷校勘記》 、《中論注》。其中,《唐寫本玉篇殘卷校說文記》為校勘之佳作,《異語疏證》、《 兩戴禮記札疏》為注釋之佳作,《釋疾》、《字義反訓集證》則是匯集相關資料后加以 注釋的名篇。
《周秦道論發微》一書中,收有《老子疏證》、《管子四篇疏證》、《太史公論六家 要指述義》三文,篇幅占了全書一大半。這些疏證之作,本身有獨立存在的價值,但她 們主要還是為“道論”作注腳,是為正文服務的。這種疏證,顯然有別于一般注釋。
四、纂輯類
將相關聯的資料匯集到一起,可省卻讀者不少翻檢之勞。張先生在治學歷程中,善用 纂輯之法,留下不少纂輯之作,計有《聲論集要》、《經傳諸子語選》、《清儒論學語 錄》、《清儒論學文選》等10來種。尤為重要的,有以下幾種:
一為《聲論集要》,收載于《舊學輯存》中冊。張先生自少好治文字、聲韻、訓詁之 學,讀劉熙《釋名》,恍然有悟于聲訓之理,至精至確。后涉覽300年來儒先著述,發 現已多先己而言之者,于是從戴震至黃侃、錢玄同20人著述中,撮錄精語,成《聲論集 要》一卷。亦間述已意附于其尾,以見昔賢所論,固無二致。
二為《鄭雅》,收載于《鄭學叢著》。張先生治毛鄭《詩》,喜陳澧《毛傳義類》, 隱括有條例,與《爾雅》相表里。效其體,成《鄭箋義類》,后治《三禮》,鉆研鄭注 ,仍斯例為《三禮鄭注義類》。復博采鄭氏群經佚注之可考者,裒錄為《鄭氏佚注義類 》。后合此數種,成《鄭雅》19篇。《鄭雅》體例,一仿《爾雅》,將鄭玄注解匯編, 使“北海精詣,粲然大備”。張先生在序中對素志克酬,喜不自禁,稱“此編訓詁名物 之繁賾,倍蓰于《毛傳》、《爾雅》、《說文》。茍能貫通鄭學,則群經莫不迎刃而解 。斯一編也,不第六藝之鈐鍵,抑亦考古之淵藪也。”[10](P198)
三為《周秦諸子政論類要》,收載于《舊學輯存》中冊。張先生博考前史,深服歷代 大政治家之所施為,以其雄偉之氣魄,毅然任天下之重,堅于自信,不以世俗毀譽動其 心;剛斷果毅,卓然有以自見于當時而永傳于后世。若霍光、諸葛亮、王猛、魏徵、王 安石、張居正之儕,治國處事,無不具有法家精神。實皆自周秦法家書中取得政治理論 以自敦厲者。法家職志,以富強國家為已任,管、商其中之尤魁杰者耳。周秦諸子書中 言富強之術者多,有以功業自白于世者,有以言論垂之久遠者,皆坐言而可起行,宜其 為后世政治家所服膺而不欲斯須舍棄。遂用前代錄要之法,成《周秦諸子論政類要》三 編。上編為《周秦諸子政論之總精神》,中編為《周秦諸子論法》,下編為《周秦諸子 論政》。每編之下,又各立8至10個小題以相統括。于是周秦諸子之言治道者,精義名 言,多在其中。
以上幾種纂輯之作,實際上已經將鈔書和著述合為一體。中有所主,非一般泛濫無歸 的比輯纂錄之編可比。
從張舜徽先生的歷史文獻學理論及其實踐,我們不難體會到,歷史文獻學的研究范圍 是極其廣闊的。在任何一個領域沉潛書卷,伏案數十載,都可取得世人注目的成就。即 使是在傳統的研究領域,用傳統的著述方式,也可以推陳出新,別開生面。他格外重視 文獻學工作者的胸襟和視野,早年談校讎學,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鵠的,晚年 談文獻學,強調要做總結性的工作。他的不少具體論述,或許有著缺陷,但他堅持“中 有所主”,從大處、高處著眼,把文獻整理與研究看成一種創造性勞動,終于在所有他 鉆研的課題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對于后輩文獻學工作者來說,張舜徽先生的治學途徑值 得借鑒,他的歷史文獻學理論及其實踐也應成為人們繼續前行的一個階梯。
【張舜徽先生歷史文獻學成就述要】相關文章:
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研討會述要06-03
淺談《詩經》的藝術成就及影響論文04-13
歷史教學開題報告06-28
從失語走向歷史透視05-30
歷史小論文怎么寫?10-11
歷史小論文(精選23篇)07-18
淺析張派京劇藝術論文05-24
杭徽高速公路留下互通A匝道橋第八聯31號墩端橫梁加固實踐06-10
“上帝死了”及其歷史意義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