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梳理法律的核心要素──讀《法律的概念》
英國學者哈特(H.L.A.Hart)的《法律的概念》(Hart,1961,1994)[1],為學人視為法理學經典中的經典,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在英美乃至整個西方,這一文本又成為分析實證品格的法理學或轉向或變革或發展的承上啟下的敘事作品。它弱化了一個舊語境,開啟了一個新語境。在新的語境中,分析實證法理學具有了新的敘事策略和新的話語訴求。在中國讀者的知識狀態中,理解這些則需要一種語境融合中的新的解讀。
一、法律的定義
“本書的目的不是提供一個法律的定義,而是提供一個國內法律制度獨特結構的更佳分析和一個作為社會現象的法律、強制和道德之間的類似與區別的更佳理解,以此促進法律理論的發展”(Hart,1961:17)。[2]這是《法律的概念》中提綱挈領的一段敘述詞語。
研究法理學,首要的問題是研究法律的性質。研究法律的性質時常被視為尋找和界說法律的定義。不奇怪,在中國的法律知識狀態中,如果一個文本被稱為《法律的概念》而其中不存在一個法律的定義,那么,其何以可稱為《……的概念》?何以為讀者提供一個區別法律和其他社會現象的手段工具?遑論法律理論的發展?中國的法律話語一般會有這樣一個暗示:各種分析性質的法理學研究的起點應指向法律定義的界說。《阿奎那政治著作選》說:作為一個定義,法律“不外乎是對于種種有關公共幸福的事項的合理安排,由任何負有管理社會之責的人予以公布”(阿奎那,1982年:頁106)。[3]邊沁的《法律通論》說:“可以將法律界定為一國主權者設想或采用的一系列意志宣告,其涉及某個人或某些人在一定情形下服從的行為。”(Bentham,1970:1)[4]在中國的語境中,這些論說通常被視為一種法律概念的明確闡述。雖然其內容可能不被同意,但其形式作為法律定義的一種方式則是無可質疑的。法律的定義,被看作法律論說被清晰理解的必要前提。
于是,我們的敘事方式和《法律的概念》的敘事方式之間的一個語境差異,在于“定義的看法”不同。
中國語境中法律定義的設想是建立一個法律的種差概念,即首先尋找一個族系或類(如行為規則、規范等),然后再尋找族系或類成員(如法律規則、道德規則、宗教規則)之間的差異,最后用名詞(即族系或類)之前不斷增設形容詞(差異)的敘事方式建構法律界說的模式。有文本便以為,“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并有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的,反映統治階級(即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意志的規范系統……”(孫國華等,1994年:頁79-80)[5]“法是由一定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由在一定地域內的公共權力機關以強制力保證其施行,以求確定主體的權利和義務、保護和發展特定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倪正茂, 1996年:頁22)。[6]
但是《法律的概念》認為:這種方式的“成功時常依賴尚未滿足的條件,這些條件之中的首要條件是應當存在一個更大的事物族系或類,其特征為我們所了解,其定義在界定他者時已被設定。顯然,如果對事物族系或類只有含糊或混亂的觀念,一個告訴我們某種事物屬于該族系成員的定義便無法幫助我們。就法律而言,正是這一要求決定了這種定義形式沒有用處,因為,在此不存在人們熟悉且容易理解的法律是其成員的一般范疇。在法律定義中,前述定義方式使用的最為明顯的一般范疇是行為規則這一一般事物族系。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其本身像法律的概念本身一樣令人困惑”(Hart,1961:17)。[7]《法律的概念》提醒人們注意,如果對于一個法律的類概念(如行為規則)沒有清楚的認識,當然無法清楚地了解法律的定義。依照前述的定義模式,對于一個概念的把握是無法清晰的,因為,無法最終把握可以不斷延續下去的類概念。這就如同認識大象一樣,如果想知其是什么,便需知道作為其類概念的“動物”的明確含義,而要理解“動物”是什么,便需知道其類概念“生物”的明確含義,而要理解“生物”是什么,就需進一步理解“物質”、“存在”……
不僅如此,《法律的概念》還提出了另一個反對一般法律定義模式的理由:這種簡單定義方式依賴一種默認的假設,即所有被定義為某物的事例,具有定義表示的共同特征,“但是甚至在較為一般的場合也可以發現邊緣情形的存在。這表明一般術語所指稱的若干事例具有共同特征的假設或許是個教條。術語的通常用法甚至專門用法時常是十分‘開放的’,因為這些用法并未將術語的外延限制在那些只有某些正常的并存的特征呈現出來的事例……對國際法和某些形式的原始法來說,情況就是如此。”(Hart,1961:17)[8]這里的意思是說,術語的用法具有模糊邊緣的區域,在這一區域中既不能肯定也不能排斥定義對某些對象的有效性。
根據這種“定義的看法”,《法律的概念》放逐了法律的定義。這是告訴讀者,推進法律理解的首要契機便是從“法律定義”的困擾與爭論中擺脫出來。
在《法律的概念》之后的分析法理學的語境中,法律的定義成為眾多法理學文本中的“缺席”。英國學者拉茲(Joseph Raz)的《法律制度的概念》()[9]和《法律的權威》()[10],麥考密克(Neil MacCormick)的《法律推理與法律理論》()[11]和《制度法論》()[12],美國學者戈爾丁(Martin Golding)的《法律哲學》()[13]……作為分析法理學的重要文本,不再界說傳統意義的法律定義。當然,這不是說在《法律的概念》之后才出現了法律定義的全方位放逐,而是說,在其中闡述的反對定義方式的理由里,分析品格的法律話語自認為可以獲得勝過“定義方式”的“他者”敘事手段,從而以另外的角度議論法律的性質。
面對顛覆“法律定義”的話語,中國語境的論者自然可以提出一個反駁:如果這種定義方式不能獲得清晰的認識,那么其他敘事手段同樣不能成功,因為,任何敘事方式都是由陳述而且都是由語詞構成的,而任何陳述或語詞都將面臨被其他語詞解釋的問題。換言之,如果對陳述或語詞沒有清晰的認識,對敘事方式本身便不會有清晰的認識。而對陳述和語詞的澄清認識,總存在著“不斷追蹤”因而無法清晰的問題。比如,針對“被繼承人死亡繼承開始”這一陳述,如果要想獲得清晰的認識,就需理解“繼承”這一語詞的含義。而要理解“繼承”的含義就要理解“獲得”、“接受”、“轉移”等語詞的含義……這一過程是個“不斷追蹤”的過程。另一方面,中國語境論者還可提出一個反駁:如果一個定義不能涵蓋邊緣區域的外延對象,則其他敘事手段也將面臨同樣的問題。因為,后者在說明一些對象的同時也將不能肯定地說明其他一些具有類似性質但又具有某些差異性質的對象。就此而論,不能認為可能存在的其他敘事手段要比“法律定義”來得有效或成功。進而言之,如果其他敘事手段可以存在,“法律的定義”也有存在的理由。
上述反駁是言之有理的。而且,它又意味著在《法律的概念》提出的批評包含著自我顛覆:獲得清晰認識的目的只能導向不能獲得清晰的認識。這是說,《法律的概念》的初衷是通過反省“法律的定義”方式以獲得認識法律性質的清晰敘事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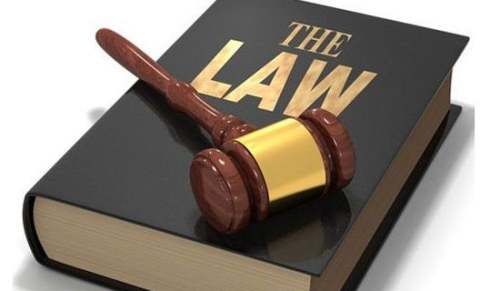
【梳理法律的核心要素──讀《法律的概念》】相關文章:
法律的概念性01-14
論法律樣式的概念及其解釋意義03-20
法律權威性的概念和來源分析01-01
抽樣取證的概念和適用法律基礎03-21
論法律行為概念的緣起與法學方法(五)03-18
論法律行為概念的緣起與法學方法(六)03-24
法律語言與法律文化論03-24
《法律的概念》讀后感03-18
法律的道路03-18